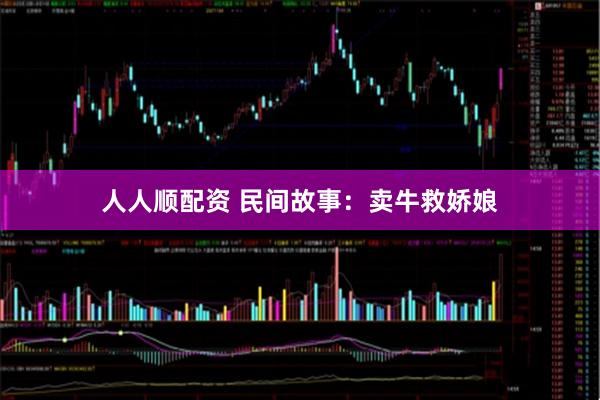
列位看官,咱今儿个讲一段青林峪的旧事。主角是个天生不能言语的汉子,偏凭着一副肝胆,干出了桩惊动四邻的义举。这事儿里有凶险,有暖意,您且坐稳了,听我慢慢道来。
那夜正是月黑风高,哑汉陈默刚躺到炕上,就听见院墙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他心里咯噔一下,悄悄凑到窗缝往外瞅。
好家伙,十来个蒙面的壮汉,正抬着一口黑沉沉的棺材,闷头往后山的乱葬岗挪。更邪乎的是,那棺材里竟隐隐传出呜呜咽咽的动静。
分明是有人被堵了嘴,在里头拼命挣扎!哪是什么送葬,这是活生生要埋人啊!陈默摸起墙根的砍柴刀,掖在腰后,猫着腰就跟了上去。
到了乱葬岗,汉子们抡起锄头,几下就刨出个深坑,吆喝着就要把棺材往坑里推。领头的恶声骂道:“清沅,休怪兄弟们心狠,谁让你脸生恶疮,污了咱们寨子的名声!”
展开剩余85%这话入耳,陈默的血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。他再也忍不住,猛地从树后蹿出来,张开双臂挡在棺材前,咿咿呀呀地朝着汉子们比划,急得满脸通红。
汉子们定睛一看,原来是个哑巴,顿时没了忌惮。一个小喽啰上前,伸手就把陈默推了个趔趄,恶狠狠地啐道:“哑巴多管闲事,再挡道,连你一块儿填坑!”
陈默被推得撞在棺材上,眼看那黑棺就要坠入深坑,他红着眼抄起地上的石头,朝着汉子们就砸了过去。汉子们顿时火起,撸起袖子就要动手。
领头的却摆了摆手,不耐烦地喝道:“别磨蹭!赶紧埋了走人,免得天亮露了马脚!” 几人不敢耽搁,七手八脚地填土,插了块无字木牌,转眼就溜得没影了。
陈默扑到那新堆的坟包上,伸出双手拼命地刨土。锋利的石子划破了他的掌心,鲜血混着泥土糊了满手,他却浑然不觉。
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挖,快把人救出来!就这么硬生生刨了一个多时辰,冰冷的棺盖总算露了出来。
陈默用尽全身力气,“哐当” 一声推开棺盖。里头躺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,嘴被粗布堵着,手脚被麻绳捆得死死的,半边脸上的恶疮渗着黄水,看着格外揪心。
他慌忙扯掉姑娘嘴里的布条,解开捆着的绳索,颤抖着手指探了探她的鼻息 —— 还有气!陈默心头一松,抱起姑娘就往家跑。
山路崎岖,夜风呼啸,姑娘的发丝蹭过他的脖颈,他却只觉得心头突突直跳,脚下丝毫不敢放慢。
好不容易跑回自家的土坯房,陈默点亮油灯,昏黄的灯光下,才看清姑娘的模样。眉眼本是清秀的,只是被脸上的恶疮掩了颜色。
他端来一盆温热的清水,撕了块干净的粗布,蘸着水小心翼翼地擦拭姑娘脸上的脓水。刚擦了没几下,姑娘就悠悠转醒了。
睁眼看到陌生的陈默,姑娘吓得浑身一颤,缩成一团,声音发颤地问:“你是谁?这是哪里?我…… 我怎么会在这儿?”
陈默急得满头大汗,比划着抬棺、刨土的动作,又指了指门外的方向,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,恨不得把方才的事全说清楚。
姑娘盯着他的动作看了半晌,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。她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,“扑通” 一声跪在陈默面前,连连磕头:“恩人!是你救了我!”
“我叫清沅,寨里人说我得了麻风病,是不治的脏病,竟要把我活活埋了!” 姑娘说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,混着脸上未干的黄水,看着让人心疼。
陈默虽不知麻风病是啥,但他知道,见死不救,枉为人。他重重地点了点头,找了块青布,轻轻给清沅裹住脸,又牵出了院里的老黄牛。
这老黄牛可是陈默的命根子。爹娘走得早,他一个人孤苦伶仃,全靠这头牛耕地犁田,换些粮食度日。牛通人性,平日里耕地会放慢脚步,歇晌时会拿脑袋蹭他的胳膊,比亲人还亲。
陈默牵着牛,拉着清沅,一步一步往山下的镇子走。天刚蒙蒙亮,镇上的集市已经有了人声。陈默牵着牛,径直往牛市走去。
买牛的商贩见这牛身强体壮,是个好劳力,当下就给了个公道的好价钱。陈默攥着沉甸甸的银子,却不敢回头看老黄牛被牵走的方向,怕自己忍不住落泪。
他拉着清沅,脚步匆匆地往镇上的郎中铺跑。须发花白的老郎中仔细端详了清沅的脸,又给她把了脉,捋着胡子笑了:“姑娘莫怕,这不是麻风病,只是热毒郁结的恶疮,敷几副药就能好。”
这话一出,清沅当场就哭出了声。她转过身,抱着陈默的胳膊,哭得泣不成声。陈默站在原地,傻呵呵地笑,露出两排白牙,笨拙地拍着她的背,眼里满是欢喜。
从那以后,清沅就留在了陈默的土坯房里。她洗衣做饭,缝补衣裳,又跟着陈默下地干活,把那漏风的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,处处透着烟火气。
陈默的日子,也终于从孤孤单单,变得热热闹闹。几个月后,清沅脸上的恶疮彻底好了,露出一张清秀的脸庞,比从前还要耐看几分。
她看着陈默老实本分,待自己又掏心掏肺的好,终于红着脸,小声对他说:“陈默哥,我这辈子,就跟了你吧!”
陈默愣在原地,半晌才反应过来。他高兴得像个孩子,一把抱起清沅,在院子里转了好几个圈,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,满是欢喜。
他请了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作证,简简单单办了一桌酒席,两人就算是成了亲。婚后的日子,过得比蜜还甜。
陈默每次下地回来,总不忘在路边掐一朵野花,带回家插在清沅的发间。清沅夜里就坐在灯下,给陈默缝补磨破的衣裳,两人虽少言语,却有着说不尽的默契。
日子一晃,就过了大半年。这天吃饭时,清沅忽然捂着嘴,干呕了好几下。陈默吓了一跳,连忙放下碗筷,就要拉着她去镇上找郎中。
清沅红着脸,拉住他的手,小声说:“我没事,许是…… 许是有了身孕了。” 陈默愣了半晌,才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。
他高兴得手舞足蹈,一把抱起清沅,在院子里跑了一圈又一圈。山里的风拂过脸颊,带着稻花的清香,竟比蜜还要甜几分。
从那以后,陈默每天晚上都要趴在清沅的肚子上,听里头的动静,脸上满是期待的笑容。可天有不测风云,谁也没料到,劫难竟会悄然而至。
清沅怀足八个月的时候,那天夜里,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,冷汗湿透了衣裳。陈默慌得手足无措,背起她就要往山下跑。
清沅却死死拉住他的衣角,虚弱地说:“夜路太险,你…… 你陪着我就好,我能撑住。” 陈默急得掉眼泪,烧了滚烫的热水,又找了干净的布条。
他蹲在床边,紧紧攥着清沅的手,一刻也不敢松开。清沅咬着牙,忍着钻心的疼,额头上的冷汗像断了线的珠子,却还强撑着,对他露出一抹安慰的笑容。
就这么熬啊熬,熬到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,一声响亮的啼哭,突然划破了山谷的寂静。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子,哭声洪亮得很。
陈默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婴孩,看着他通红的小脸,笑着笑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给孩子取名叫陈实,盼着他这辈子,都能踏踏实实,做个好人。
可清沅生完孩子后,身子却一天比一天弱。起初只是偶尔咳嗽几声,后来竟连下床走路的力气都没了。陈默背着她,跑遍了周边的村镇,找了十几个郎中。
可那些郎中,要么摇着头叹气,要么干脆闭门不见。最后一位老郎中,摸着胡子叹了口气:“她这是产后亏空太甚,伤及了根本,怕是…… 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”
这话像一盆冷水,浇得陈默从头凉到脚。他不信,偏不信!他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,全都换成了银子,买了最好的补药,一勺一勺喂给清沅喝。
他每天守在床边,寸步不离。清沅喝药,他就亲自熬;清沅喝粥,他就亲自喂;夜里睡觉,他就紧紧攥着她的手,生怕一松手,她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清沅的脸,一天比一天苍白,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深秋的一个午后,难得的好阳光。清沅让陈默扶着她,坐在门口的石凳上。
她望着远处金灿灿的稻田,轻声说:“你看,稻子熟了,今年又是个好收成。等阿实长大了,让他…… 让他好好种地,做个像你一样的好人。”
陈默点着头,把她搂得更紧了些。清沅抬起手,轻轻摸着他的脸,声音轻得像一缕烟:“我走后,你要好好带大阿实,别…… 别让他受委屈。”
陈默拼命摇头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砸在清沅的手背上。清沅看着他,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,然后,眼睛就慢慢闭上了,手却还紧紧攥着他的衣角。
陈默抱着她,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,从日出,一直坐到夕阳染红了远处的山岗。后来,陈默一个人,又当爹又当妈,把陈实拉扯长大。
陈实和他爹一样,老实本分,心肠热乎,只是口齿伶俐,能说会道。他常听陈默比划着,讲起清沅的故事,每次都听得红了眼眶。
陈实长大后,娶了媳妇,把家里的土坯房,翻新成了亮堂堂的砖瓦房。他生了三个孩子,每次给孩子们讲故事,总要说:“你们的爷爷是个哑人,却是这世上最勇敢、最善良的好人。咱们陈家的子孙,都要学他的样,多行善事,莫问前程。”
列位看官,这故事讲到这儿,也就算完了。陈默一个不能言语的哑汉,敢冒着性命之忧,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;又舍得卖掉自己的命根子,去救她的性命。
这份善良,这份勇气,比那黄金美玉,还要金贵百倍。清沅虽遭族人抛弃,却遇上了陈默,两人相守一场,育有一子,也算不枉此生。
这世上的事,本就是如此。善良从不会白费,你种下的善因,总有一天,会结出善果。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。多行善事,少做恶事,老天爷自会给你一份安稳。
发布于:吉林省展鹏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